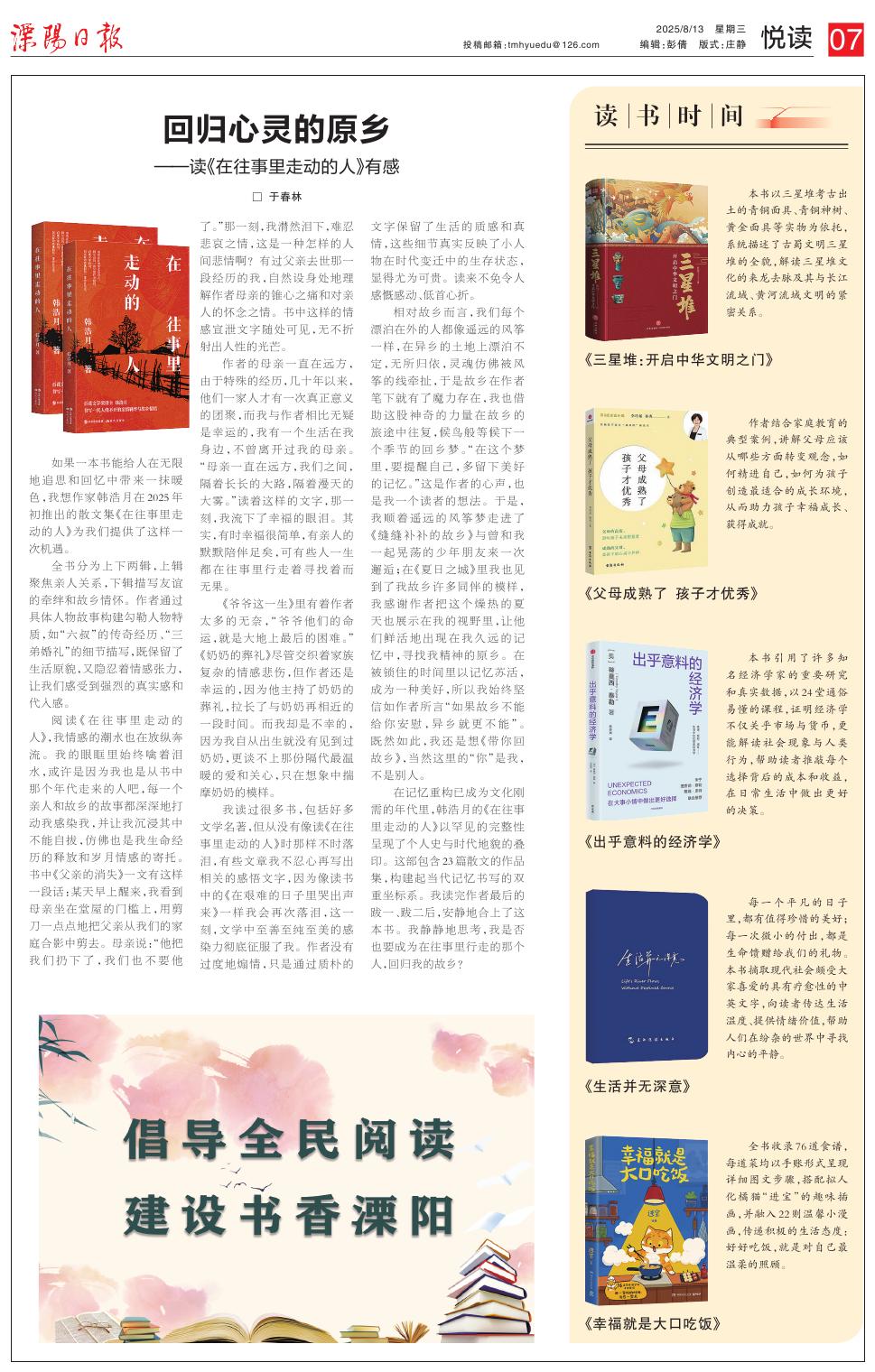

回归心灵的原乡
——读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有感
□ 于春林

如果一本书能给人在无限地追思和回忆中带来一抹暖色,我想作家韩浩月在2025年初推出的散文集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机遇。
全书分为上下两辑,上辑聚焦亲人关系,下辑描写友谊的牵绊和故乡情怀。作者通过具体人物故事构建勾勒人物特质,如“六叔”的传奇经历、“三弟婚礼”的细节描写,既保留了生活原貌,又隐忍着情感张力,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真实感和代入感。
阅读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,我情感的潮水也在放纵奔流。我的眼眶里始终噙着泪水,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从书中那个年代走来的人吧,每一个亲人和故乡的故事都深深地打动我感染我,并让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,仿佛也是我生命经历的释放和岁月情感的寄托。书中《父亲的消失》一文有这样一段话:某天早上醒来,我看到母亲坐在堂屋的门槛上,用剪刀一点点地把父亲从我们的家庭合影中剪去。母亲说:“他把我们扔下了,我们也不要他了。”那一刻,我潸然泪下,难忍悲哀之情,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悲情啊?有过父亲去世那一段经历的我,自然设身处地理解作者母亲的锥心之痛和对亲人的怀念之情。书中这样的情感宣泄文字随处可见,无不折射出人性的光芒。
作者的母亲一直在远方,由于特殊的经历,几十年以来,他们一家人才有一次真正意义的团聚,而我与作者相比无疑是幸运的,我有一个生活在我身边,不曾离开过我的母亲。“母亲一直在远方,我们之间,隔着长长的大路,隔着漫天的大雾。”读着这样的文字,那一刻,我流下了幸福的眼泪。其实,有时幸福很简单,有亲人的默默陪伴足矣,可有些人一生都在往事里行走着寻找着而无果。
《爷爷这一生》里有着作者太多的无奈,“爷爷他们的命运,就是大地上最后的困难。”《奶奶的葬礼》尽管交织着家族复杂的情感悲伤,但作者还是幸运的,因为他主持了奶奶的葬礼,拉长了与奶奶再相近的一段时间。而我却是不幸的,因为我自从出生就没有见到过奶奶,更谈不上那份隔代最温暖的爱和关心,只在想象中揣摩奶奶的模样。
我读过很多书,包括好多文学名著,但从没有像读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时那样不时落泪,有些文章我不忍心再写出相关的感悟文字,因为像读书中的《在艰难的日子里哭出声来》一样我会再次落泪,这一刻,文学中至善至纯至美的感染力彻底征服了我。作者没有过度地煽情,只是通过质朴的文字保留了生活的质感和真情,这些细节真实反映了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状态,显得尤为可贵。读来不免令人感慨感动、低首心折。
相对故乡而言,我们每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像遥远的风筝一样,在异乡的土地上漂泊不定,无所归依,灵魂仿佛被风筝的线牵扯,于是故乡在作者笔下就有了魔力存在,我也借助这股神奇的力量在故乡的旅途中往复,候鸟般等候下一个季节的回乡梦。“在这个梦里,要提醒自己,多留下美好的记忆。”这是作者的心声,也是我一个读者的想法。于是,我顺着遥远的风筝梦走进了《缝缝补补的故乡》与曾和我一起晃荡的少年朋友来一次邂逅;在《夏日之城》里我也见到了我故乡许多同伴的模样,我感谢作者把这个燥热的夏天也展示在我的视野里,让他们鲜活地出现在我久远的记忆中,寻找我精神的原乡。在被锁住的时间里以记忆苏活,成为一种美好,所以我始终坚信如作者所言“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,异乡就更不能”。既然如此,我还是想《带你回故乡》,当然这里的“你”是我,不是别人。
在记忆重构已成为文化刚需的年代里,韩浩月的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以罕见的完整性呈现了个人史与时代地貌的叠印。这部包含23篇散文的作品集,构建起当代记忆书写的双重坐标系。我读完作者最后的跋一、跋二后,安静地合上了这本书。我静静地思考,我是否也要成为在往事里行走的那个人,回归我的故乡?

